记忆中的“麦假”
2024年07月01日
字数:1283
版次:04
坐着大巴车从胶东半岛往鲁西南家乡的方向,透过高速路两旁高大的杨树往远方眺望,一片片麦田随着车轮转动由青黄逐渐变为金黄。临近农历五月,芒种支棱着闪闪麦芒、裹挟着金色麦浪翻滚不息,我仿佛嗅到风中阵阵麦子的芳香,关于小时候放“麦假”的记忆,继小满的蛰伏之后,纷沓而至。
“麦假”又称“芒假”,大约两周时间,一般是放在“芒种”小麦成熟的时节。在农村收割机还比较稀缺的年代,麦收的时间非常紧张,乡镇学校的老师和家里的大人集中利用十多天时间赶在下雨前抢完麦收。生长在农村,劳动是我们的必修课,麦假里,年幼的我们俨然是麦收主战场的“小配角”,拾麦穗、撮麦籽、撑布袋、晒麦看场、往地里送饭菜茶水,同样忙得不亦乐乎。印象中收麦季的太阳总是火辣辣的,一把把锃亮的镰刀在大人手里以弧线的形式收割前进,孩童们跟在大人后面漫无目的地拾着麦穗。偶尔抬起头,目光越过父母弓起的脊梁,田垄尽头杨树下的阴凉总是遥不可及。远处传来聒噪的蝉鸣,阳光炙烤下挥之不去的汗水,被晒得发红的脸庞,麦芒扎在身体里的灼热、刺痛混合着一垄垄收割的麦田,伴随着麦收的喜悦充满了整个夏天。
麦收前一般会在地头先割出一片空地,经过平整、压实做好“打麦场”,收割后的麦子陆续运到麦场,通过脱粒机或者拖拉机拉着石磙碾压完成脱粒工序。脱粒机和石磙碾压留下来的混合着麦糠的麦粒堆成一个个小堆,大人们拉开架势,稳稳站好,用木锨拖着用力向上一扬,麦糠散去,麦粒落下,父母用最简单的姿势把这些走过四季的希望扬在肩上,落在奔跑中的孩童身上。“扬场”后就是“晒场”,孩子们用自己的脚丫充当天然工具跟在大人后面,把一堆堆麦粒有序摊平,麦粒由潮湿到干燥,脚下不仅有阳光的温度,更有丰收的踏实与厚重。装麦子环节轮到我们大显身手的时候,端着胳膊,手臂用力帮大人撑开布袋,一颗颗饱满的麦粒宛如金黄色的瀑布倒进布袋。终于,麦子沿着节气的齿轮兜兜转转,顺着古老农谚几经工序颗粒归仓。
麦田地的午饭前,孩童们提前回家把爷爷奶奶准备好的饭菜用挎篮拿到场里,更多的时候大人们总是沉默不语,趁着吃完午饭的时间抓紧躺在麦秸堆里休息一会,这时的“打麦场”俨然成为孩子们嬉戏的游乐场。我们在麦秸堆旁奔跑玩耍、捉迷藏,大家你追我赶,看谁爬得更高,钻得更深。有天下午我玩累后枕着麦秸闻着麦香进入梦乡,睡梦中没有写不完的作业、背不完的课文,睁眼太阳早已落下西山,天空蒙上一层灰色,大人们在场地里收拾农具,把一袋袋麦子装车拉回家。直到月亮出来,星星布满天空,我们走过覆满麦茬的地垄,走出月光明亮的田野,走回炊烟袅袅的家中。
后来父母离开农村搬进城市,工作后我也离开家乡定居蓬莱十余年,回乡的日子屈指可数,眼前景色也由宽广的麦田变成一望无垠的大海,余华老师在纪录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里描述自己被洋流冲着远离陆地的场景“洋流推着我往前,我只能一直往回游,一直游”。漫长岁月里旧日的暖色仿佛褪去,呈现出一副陌生的模样,就像我经常看到的海水,混着泥沙,泛着青黄色,经历过“麦假”的孩童也已步入中年,童年的“打麦场”仿佛在告诉我,随风翻滚的麦浪,是游子心中永远的家乡。
“麦假”又称“芒假”,大约两周时间,一般是放在“芒种”小麦成熟的时节。在农村收割机还比较稀缺的年代,麦收的时间非常紧张,乡镇学校的老师和家里的大人集中利用十多天时间赶在下雨前抢完麦收。生长在农村,劳动是我们的必修课,麦假里,年幼的我们俨然是麦收主战场的“小配角”,拾麦穗、撮麦籽、撑布袋、晒麦看场、往地里送饭菜茶水,同样忙得不亦乐乎。印象中收麦季的太阳总是火辣辣的,一把把锃亮的镰刀在大人手里以弧线的形式收割前进,孩童们跟在大人后面漫无目的地拾着麦穗。偶尔抬起头,目光越过父母弓起的脊梁,田垄尽头杨树下的阴凉总是遥不可及。远处传来聒噪的蝉鸣,阳光炙烤下挥之不去的汗水,被晒得发红的脸庞,麦芒扎在身体里的灼热、刺痛混合着一垄垄收割的麦田,伴随着麦收的喜悦充满了整个夏天。
麦收前一般会在地头先割出一片空地,经过平整、压实做好“打麦场”,收割后的麦子陆续运到麦场,通过脱粒机或者拖拉机拉着石磙碾压完成脱粒工序。脱粒机和石磙碾压留下来的混合着麦糠的麦粒堆成一个个小堆,大人们拉开架势,稳稳站好,用木锨拖着用力向上一扬,麦糠散去,麦粒落下,父母用最简单的姿势把这些走过四季的希望扬在肩上,落在奔跑中的孩童身上。“扬场”后就是“晒场”,孩子们用自己的脚丫充当天然工具跟在大人后面,把一堆堆麦粒有序摊平,麦粒由潮湿到干燥,脚下不仅有阳光的温度,更有丰收的踏实与厚重。装麦子环节轮到我们大显身手的时候,端着胳膊,手臂用力帮大人撑开布袋,一颗颗饱满的麦粒宛如金黄色的瀑布倒进布袋。终于,麦子沿着节气的齿轮兜兜转转,顺着古老农谚几经工序颗粒归仓。
麦田地的午饭前,孩童们提前回家把爷爷奶奶准备好的饭菜用挎篮拿到场里,更多的时候大人们总是沉默不语,趁着吃完午饭的时间抓紧躺在麦秸堆里休息一会,这时的“打麦场”俨然成为孩子们嬉戏的游乐场。我们在麦秸堆旁奔跑玩耍、捉迷藏,大家你追我赶,看谁爬得更高,钻得更深。有天下午我玩累后枕着麦秸闻着麦香进入梦乡,睡梦中没有写不完的作业、背不完的课文,睁眼太阳早已落下西山,天空蒙上一层灰色,大人们在场地里收拾农具,把一袋袋麦子装车拉回家。直到月亮出来,星星布满天空,我们走过覆满麦茬的地垄,走出月光明亮的田野,走回炊烟袅袅的家中。
后来父母离开农村搬进城市,工作后我也离开家乡定居蓬莱十余年,回乡的日子屈指可数,眼前景色也由宽广的麦田变成一望无垠的大海,余华老师在纪录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里描述自己被洋流冲着远离陆地的场景“洋流推着我往前,我只能一直往回游,一直游”。漫长岁月里旧日的暖色仿佛褪去,呈现出一副陌生的模样,就像我经常看到的海水,混着泥沙,泛着青黄色,经历过“麦假”的孩童也已步入中年,童年的“打麦场”仿佛在告诉我,随风翻滚的麦浪,是游子心中永远的家乡。
(作者单位:山东蓬莱公司)

 首页
首页 上一期
上一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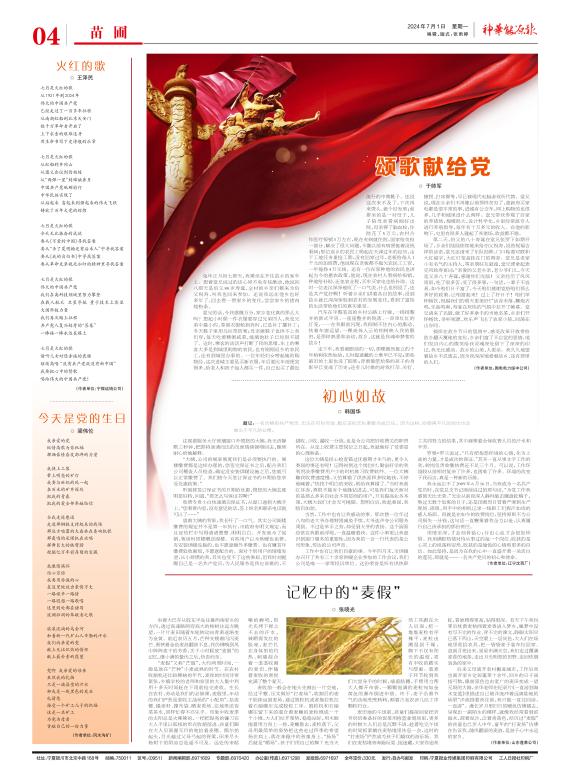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