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芯里的光
2025年10月09日
字数:1509
版次:04
东北农村的冬夜,黑得沉实,连风都裹着寒气往屋里钻。老屋炕沿悬着的玻璃罩煤油灯,是寒夜里唯一的光——灯芯烧得泛红,把光缩成一小团,刚好罩住父亲批改的作业本、母亲的针线笸箩,还有我面前的描红本。父亲握笔的手刚劲有力,笔尖划过纸页的“沙沙”声,混着母亲纳鞋底时线绳穿过布眼的“噗噗”声,在灯影里绘成了一幅温暖画面。我攥着铅笔头,看灯花“噼啪”爆开又熄灭,揉着发酸的眼睛问:“娘,啥时候能有电灯啊?这样写作业,字都看不清楚。”母亲放下针线,用指腹轻轻揉我的眼窝,指尖的顶针在灯下发亮:“等俺闺女长大了,日子准能好起来,到时候屋里亮得能照见人影,再也不用揉眼睛。”
后来我长大了,却没能陪母亲等到屋里“亮得照见人影”的那天。因为我穿上了国家能源集团的蓝灰色工装,站到了发电厂的厂房,成了给千万家庭“造光明”的人。第一次跟着师傅去现场巡检,高大的汽轮机在眼前轰鸣,管道上的保温层带着温热,仪表盘上的数字跳得比当年的煤油灯芯还鲜活。师傅指着汽轮机旁的压力表,声音裹在机器声里却格外清晰:“咱干的是‘能源报国’的活儿,这表上的数差一丝,发电效率就受影响,说不定谁家的暖气就凉了,孩子写作业的灯就暗了。”我摸着胸前的工作牌,指尖蹭过“国家能源”四个字,突然想起母亲纳鞋底的模样——她当年一针一线纳的是我的温暖,如今我盯着的每一组数据、拧紧的每一颗螺丝,守的是千万人的温暖。厂房里的风裹着机器的热气吹过,好像把母亲当年的话也捎了来,轻得落在耳边就化了。
加班是电厂人的常态,尤其到了保供关键期。去年寒潮最猛的那几天,厂里接到紧急指令,我们在锅炉厂房和汽机平台间来来回回跑了三天三夜。监控画面里锅炉里跳动的火焰,像千万团小太阳,把煤炭的热量变成电能,顺着电缆往远方送。午夜巡查完设备回来,我摸出兜里的旧照片——那是母亲六十岁生日拍的,她坐在老屋炕边,新烫的卷发衬得脸格外精神,身后窗台上,那盏煤油灯擦得锃亮,摆得端端正正。盯着照片里母亲的笑容,恍惚间像听见她的声音:“闺女,累了就喝口热水,别硬扛。”瞬间,手里的点检仪也攥得更紧——我知道,多查一次阀门、多测一回温度,就是在替母亲圆当年的盼,就是在践行“奉献清洁能源,创造美好生活”的承诺,让更多地方不用在寒夜里盼光。
第一次独立消缺的那天,天刚蒙蒙亮,我蹲在给水泵旁,额头上的汗滴在冰凉的设备外壳上,很快被厂房的热气烘干。扳手拧动螺栓的“咔嗒”声,在清晨的厂房里格外清晰。当故障排除,压力表的指针缓缓回升到正常区间,我抬起头,晨光正好从厂房的高窗照进来,落在管道上,映出一道道亮闪闪的光。那一刻,突然想起母亲给我补衣服的场景——她总把破洞补得整整齐齐,针线走得又密又匀,补好的衣服穿在身上,像没破过。原来我们都在“补”:母亲补的是我的旧衣,怕我冻着;我补的是发电设备的“病灶”,怕千万人冷着、黑着。
今年清明回老家,村里的路灯亮得晃眼,家家户户的窗里都透着暖光。邻居大娘拉着我的手,往我兜里塞刚煮好的鸡蛋:“你娘要是知道你如今在电厂‘造电’,让咱这儿冬天不冷、夜里不黑,肯定得笑醒。”我走到老屋炕边,窗台上的煤油灯还在,只是积了层薄尘。我用袖子轻轻擦了擦玻璃罩,里面的灯芯早已干枯,却好像还能看见当年那团昏黄的光,看见母亲坐在灯旁,笑着说“日子会好起来”。
从煤油灯旁盼光明的小女孩,到发电厂里“造”光明的工人,我走过的路,正是能源事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路。我守护的每一台设备、每一缕电流,都是母亲当年期盼的光,是照亮千万家庭的光。往后的日子,我还会握紧手中的点检仪,在厂房的设备间稳稳走下去——娘,您看,现在的日子,真的像您说的那样,亮得能照见人影了;您没来得及见的光明,我替您送到了千万家。
(作者单位:吉林双辽公司)
后来我长大了,却没能陪母亲等到屋里“亮得照见人影”的那天。因为我穿上了国家能源集团的蓝灰色工装,站到了发电厂的厂房,成了给千万家庭“造光明”的人。第一次跟着师傅去现场巡检,高大的汽轮机在眼前轰鸣,管道上的保温层带着温热,仪表盘上的数字跳得比当年的煤油灯芯还鲜活。师傅指着汽轮机旁的压力表,声音裹在机器声里却格外清晰:“咱干的是‘能源报国’的活儿,这表上的数差一丝,发电效率就受影响,说不定谁家的暖气就凉了,孩子写作业的灯就暗了。”我摸着胸前的工作牌,指尖蹭过“国家能源”四个字,突然想起母亲纳鞋底的模样——她当年一针一线纳的是我的温暖,如今我盯着的每一组数据、拧紧的每一颗螺丝,守的是千万人的温暖。厂房里的风裹着机器的热气吹过,好像把母亲当年的话也捎了来,轻得落在耳边就化了。
加班是电厂人的常态,尤其到了保供关键期。去年寒潮最猛的那几天,厂里接到紧急指令,我们在锅炉厂房和汽机平台间来来回回跑了三天三夜。监控画面里锅炉里跳动的火焰,像千万团小太阳,把煤炭的热量变成电能,顺着电缆往远方送。午夜巡查完设备回来,我摸出兜里的旧照片——那是母亲六十岁生日拍的,她坐在老屋炕边,新烫的卷发衬得脸格外精神,身后窗台上,那盏煤油灯擦得锃亮,摆得端端正正。盯着照片里母亲的笑容,恍惚间像听见她的声音:“闺女,累了就喝口热水,别硬扛。”瞬间,手里的点检仪也攥得更紧——我知道,多查一次阀门、多测一回温度,就是在替母亲圆当年的盼,就是在践行“奉献清洁能源,创造美好生活”的承诺,让更多地方不用在寒夜里盼光。
第一次独立消缺的那天,天刚蒙蒙亮,我蹲在给水泵旁,额头上的汗滴在冰凉的设备外壳上,很快被厂房的热气烘干。扳手拧动螺栓的“咔嗒”声,在清晨的厂房里格外清晰。当故障排除,压力表的指针缓缓回升到正常区间,我抬起头,晨光正好从厂房的高窗照进来,落在管道上,映出一道道亮闪闪的光。那一刻,突然想起母亲给我补衣服的场景——她总把破洞补得整整齐齐,针线走得又密又匀,补好的衣服穿在身上,像没破过。原来我们都在“补”:母亲补的是我的旧衣,怕我冻着;我补的是发电设备的“病灶”,怕千万人冷着、黑着。
今年清明回老家,村里的路灯亮得晃眼,家家户户的窗里都透着暖光。邻居大娘拉着我的手,往我兜里塞刚煮好的鸡蛋:“你娘要是知道你如今在电厂‘造电’,让咱这儿冬天不冷、夜里不黑,肯定得笑醒。”我走到老屋炕边,窗台上的煤油灯还在,只是积了层薄尘。我用袖子轻轻擦了擦玻璃罩,里面的灯芯早已干枯,却好像还能看见当年那团昏黄的光,看见母亲坐在灯旁,笑着说“日子会好起来”。
从煤油灯旁盼光明的小女孩,到发电厂里“造”光明的工人,我走过的路,正是能源事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路。我守护的每一台设备、每一缕电流,都是母亲当年期盼的光,是照亮千万家庭的光。往后的日子,我还会握紧手中的点检仪,在厂房的设备间稳稳走下去——娘,您看,现在的日子,真的像您说的那样,亮得能照见人影了;您没来得及见的光明,我替您送到了千万家。
(作者单位:吉林双辽公司)

 首页
首页 上一期
上一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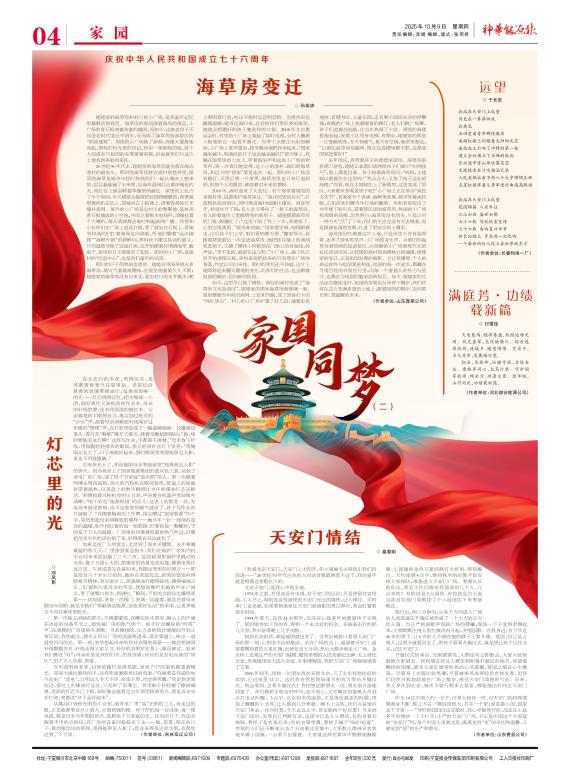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