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旅诗心家国情
2025年09月19日
字数:3030
版次:04
与几个当过兵的朋友闲聊,他们让我推荐一些军旅诗词。摊开诗词选集,从《诗经》里“与子同袍”的铿锵,到毛泽东“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豪迈,字句间跃动着金戈铁马的回响,也沉淀着孤灯照甲的温热。这些诞生于烽燧、军帐与战场的文字,从不是文人案头的风花雪月,而是将战士的铠甲与家国疆域缝合成一体。千年后的我们品读这些诗句,指尖触到的不仅是墨痕,更是无数个“我”与“国”血脉相连的心跳。
家国情怀在军旅诗词里,最先显影为《诗经·秦风·无衣》中“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铿锵。那是先秦时期,当外敌压境时,秦地将士没有计较“衣”的归属,只道“与子同袍”“与子同泽”,再一同“修我戈矛”“修我矛戟”,要带着“与子同仇”的勇气冲向战场。这哪里是简单的衣物相赠?是把个人的安危彻底融进了家国的存亡里。
汉代的边塞诗里,这份情怀又添了“舍文从武”的担当。班固《汉书》记载的《李陵歌》,“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既有征战悲壮,更藏将士对家国的牵绊。这份“以身为盾护家国”的信念,后来结出“投笔从戎”的典故。班超见匈奴扰边,掷笔叹“安能久事笔研间乎”,远赴西域三十一年护边疆安宁;伏波将军马援“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的誓言,将个人生死与家国命运熔铸一体。从李陵的身不由己到班超的主动抉择,汉代人把家国情怀写成“宁为边尘,不做书蠹”的宣言。
到了唐代,这份情怀在边塞风沙里长出了更挺拔的模样。杨炯本是书生,见“烽火照西京”,便觉“心中自不平”,直言“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不是放下笔墨,是把笔墨里的家国心,换成了剑柄上的行动力。王昌龄笔下的将士更显坚韧,“黄沙百战穿金甲”,铠甲磨得斑驳,他们记挂的从不是伤痕,只念着“不破楼兰终不还”,这誓言里没有“我要立功”,只有“楼兰不破,家国难安”的执念。王维出使塞上时,“征蓬出汉塞”的漂泊里藏着对长安的遥望,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时,壮阔里的孤独也不是为自己,是见着“都护在燕然”,既盼边事安定,又疼那些久戍不归的兵。李白写“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天山的冷刻在骨里,可将士们“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攥紧剑柄的手不肯松,只因“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比起梦里的江南春柳,家国安宁才是心头最重的秤。李贺虽属中唐,笔下的家国豪情却烈得像火。他写“黑云压城城欲摧”,敌军压境的危急里,将士们明知“霜重鼓寒声不起”,仍要“提携玉龙为君死”。这不是愚忠,是懂“黄金台上意”的分量,那是家国对将士的托底,更是将士对家国的回应,把命交出去时,念的是“城在国在”。
北宋的风沙里,范仲淹的词让家国情怀有了“文韬武略藏于胸”的模样。他戍边时写《渔家傲·秋思》,“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先绘出边塞的萧瑟,可转笔便是“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那孤城不是孤立无援,是他坐镇其中的底气。下阕“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道尽思乡与戍边的两难,却终以“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收束。这泪里没有颓丧,是将军与征夫同频的牵挂,也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襟怀在边关的落地。难怪时人说他“胸中自有万千甲兵”,不必时时舞刀弄枪,那“燕然未勒归无计”的坚守,那与征夫共担风霜的共情,早已让他成了边塞最坚实的屏障;南宋的风雨里,家国情怀藏在热血与遗憾里,更显扎心。岳飞的《满江红》里,“怒发冲冠”是见着“靖康耻,犹未雪”的急火,“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是把个人荣辱踩在脚下。他不是不爱功名,是觉得比起“臣子恨,何时灭”,那些都轻如尘埃。所以要“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要“壮志饥餐胡虏肉”,字字像钢刀劈向敌寇,末了“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又软下来,那是盼着把碎山河拼完整,给天下人一个交代;辛弃疾更像被按在纸笔间的战将。他在《破阵子》里写“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醉了才敢把剑拿出来摩挲,梦里才敢回营听吹角。醒着时,只能对着“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的旧景出神。他念“沙场秋点兵”的壮阔,想“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的酣战,连理想都直白:“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可怜白发生”一句落下来,所有豪壮都碎成叹息:不是怕老,是怕这能安家国的剑,最后只能陪着自己老在书案前;陆游一生念着家国,到老都未改。“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是少年意气,后来“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他老得跨不上战马了,可“心在天山”四个字,比任何豪言都动人。这是家国情怀最本真的模样:哪怕身不能至,心也要钉在疆土上。文天祥更是把家国情怀淬成了骨。他的《南安军》:“梅花南北路,风雨湿征衣”,国破家亡的痛刻在血里,却硬说“山河千古在,城郭一时非。”山河还在,便有希望。到最后“饿死真吾志”,宁肯赴死也要守着气节,这是把“家国”二字刻进了生死里。
时光推到近代,抗日战争的烽火里,家国情怀燃得比任何时候都烈。“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吉鸿昌将军的这首《就义诗》,如同一把利刃,划破黑暗的长空,展现出他对日寇的无比愤恨和为国家献身的坚定决心。在那山河破碎、风雨飘摇的年代,无数像吉鸿昌将军这样的英雄儿女,挺身而出,用热血和生命捍卫着祖国的尊严与领土完整。杨靖宇将军在冰天雪地中与日寇周旋,笔下“雪漫残阳,冰著寒山,铁骨傲风”,字字是冻不僵的斗志;赵一曼女士身陷囹圄仍念“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把家国重过生命的决绝,写进了带血的字句里。这些诗词没有华丽辞藻,却藏着最沉的家国痛、最烈的抗争志,国若危殆,便以血为墨,以骨为笔,也要把“守土”二字刻进天地间。
而毛泽东的军旅诗词里,家国情怀更成了改天换地的磅礴力量。长征路上,红军过五岭、越乌蒙,渡金沙、抢大渡,他写下《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在他笔下是“腾细浪”;乌蒙磅礴,不过是“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里藏着艰险,可“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里全是底气。这不是不怕难,是知道“难”的那头,是国家的新生。后来百万雄师过大江,他写《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是破竹之势,“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是换了人间的感慨,末了还醒着:“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为了家国彻底站起,这仗就得打到底。
今天,这些诗词里的家国情怀从未褪色,只是换了模样。喀喇昆仑的风雪中,“00后”战士陈祥榕写下“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用年轻的生命把雪山守成春天;江苏灌云的开山岛上,民兵王继才夫妇32年以岛为家,把“家就是国”写成最朴素的日记;实验室里,军事科研工作者为攻克“卡脖子”技术熬白了头,他们说“我们的笔,也是保家卫国的枪”。这些故事里没有“金戈铁马”的轰鸣,却同样跳动着最滚烫的心跳,就像《诗经》里的士兵不会想到,他们“与子同袍”的誓言,会在今天化作“与国同行”的日常。
“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这些军旅诗词里的家国情怀,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选择:是战场上搭起的人墙,是边疆上挺直的脊梁,是实验室里熬红的双眼。今日的我们,不必都披甲上阵,却能把“家国”二字融进日常:它是认真做好一件事的踏实,是明知艰险却仍向前的担当,是见不得家国受辱的赤诚。他的热血始终沸腾,有时变成了你递出的热粥、我留的暖灯、他守的岗位。还有我们说起祖国时,彼此眼里亮着的光。(作者单位:平庄煤业老公营子矿)
家国情怀在军旅诗词里,最先显影为《诗经·秦风·无衣》中“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铿锵。那是先秦时期,当外敌压境时,秦地将士没有计较“衣”的归属,只道“与子同袍”“与子同泽”,再一同“修我戈矛”“修我矛戟”,要带着“与子同仇”的勇气冲向战场。这哪里是简单的衣物相赠?是把个人的安危彻底融进了家国的存亡里。
汉代的边塞诗里,这份情怀又添了“舍文从武”的担当。班固《汉书》记载的《李陵歌》,“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既有征战悲壮,更藏将士对家国的牵绊。这份“以身为盾护家国”的信念,后来结出“投笔从戎”的典故。班超见匈奴扰边,掷笔叹“安能久事笔研间乎”,远赴西域三十一年护边疆安宁;伏波将军马援“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的誓言,将个人生死与家国命运熔铸一体。从李陵的身不由己到班超的主动抉择,汉代人把家国情怀写成“宁为边尘,不做书蠹”的宣言。
到了唐代,这份情怀在边塞风沙里长出了更挺拔的模样。杨炯本是书生,见“烽火照西京”,便觉“心中自不平”,直言“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不是放下笔墨,是把笔墨里的家国心,换成了剑柄上的行动力。王昌龄笔下的将士更显坚韧,“黄沙百战穿金甲”,铠甲磨得斑驳,他们记挂的从不是伤痕,只念着“不破楼兰终不还”,这誓言里没有“我要立功”,只有“楼兰不破,家国难安”的执念。王维出使塞上时,“征蓬出汉塞”的漂泊里藏着对长安的遥望,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时,壮阔里的孤独也不是为自己,是见着“都护在燕然”,既盼边事安定,又疼那些久戍不归的兵。李白写“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天山的冷刻在骨里,可将士们“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攥紧剑柄的手不肯松,只因“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比起梦里的江南春柳,家国安宁才是心头最重的秤。李贺虽属中唐,笔下的家国豪情却烈得像火。他写“黑云压城城欲摧”,敌军压境的危急里,将士们明知“霜重鼓寒声不起”,仍要“提携玉龙为君死”。这不是愚忠,是懂“黄金台上意”的分量,那是家国对将士的托底,更是将士对家国的回应,把命交出去时,念的是“城在国在”。
北宋的风沙里,范仲淹的词让家国情怀有了“文韬武略藏于胸”的模样。他戍边时写《渔家傲·秋思》,“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先绘出边塞的萧瑟,可转笔便是“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那孤城不是孤立无援,是他坐镇其中的底气。下阕“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道尽思乡与戍边的两难,却终以“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收束。这泪里没有颓丧,是将军与征夫同频的牵挂,也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襟怀在边关的落地。难怪时人说他“胸中自有万千甲兵”,不必时时舞刀弄枪,那“燕然未勒归无计”的坚守,那与征夫共担风霜的共情,早已让他成了边塞最坚实的屏障;南宋的风雨里,家国情怀藏在热血与遗憾里,更显扎心。岳飞的《满江红》里,“怒发冲冠”是见着“靖康耻,犹未雪”的急火,“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是把个人荣辱踩在脚下。他不是不爱功名,是觉得比起“臣子恨,何时灭”,那些都轻如尘埃。所以要“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要“壮志饥餐胡虏肉”,字字像钢刀劈向敌寇,末了“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又软下来,那是盼着把碎山河拼完整,给天下人一个交代;辛弃疾更像被按在纸笔间的战将。他在《破阵子》里写“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醉了才敢把剑拿出来摩挲,梦里才敢回营听吹角。醒着时,只能对着“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的旧景出神。他念“沙场秋点兵”的壮阔,想“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的酣战,连理想都直白:“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可怜白发生”一句落下来,所有豪壮都碎成叹息:不是怕老,是怕这能安家国的剑,最后只能陪着自己老在书案前;陆游一生念着家国,到老都未改。“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是少年意气,后来“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他老得跨不上战马了,可“心在天山”四个字,比任何豪言都动人。这是家国情怀最本真的模样:哪怕身不能至,心也要钉在疆土上。文天祥更是把家国情怀淬成了骨。他的《南安军》:“梅花南北路,风雨湿征衣”,国破家亡的痛刻在血里,却硬说“山河千古在,城郭一时非。”山河还在,便有希望。到最后“饿死真吾志”,宁肯赴死也要守着气节,这是把“家国”二字刻进了生死里。
时光推到近代,抗日战争的烽火里,家国情怀燃得比任何时候都烈。“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吉鸿昌将军的这首《就义诗》,如同一把利刃,划破黑暗的长空,展现出他对日寇的无比愤恨和为国家献身的坚定决心。在那山河破碎、风雨飘摇的年代,无数像吉鸿昌将军这样的英雄儿女,挺身而出,用热血和生命捍卫着祖国的尊严与领土完整。杨靖宇将军在冰天雪地中与日寇周旋,笔下“雪漫残阳,冰著寒山,铁骨傲风”,字字是冻不僵的斗志;赵一曼女士身陷囹圄仍念“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把家国重过生命的决绝,写进了带血的字句里。这些诗词没有华丽辞藻,却藏着最沉的家国痛、最烈的抗争志,国若危殆,便以血为墨,以骨为笔,也要把“守土”二字刻进天地间。
而毛泽东的军旅诗词里,家国情怀更成了改天换地的磅礴力量。长征路上,红军过五岭、越乌蒙,渡金沙、抢大渡,他写下《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在他笔下是“腾细浪”;乌蒙磅礴,不过是“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里藏着艰险,可“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里全是底气。这不是不怕难,是知道“难”的那头,是国家的新生。后来百万雄师过大江,他写《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是破竹之势,“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是换了人间的感慨,末了还醒着:“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为了家国彻底站起,这仗就得打到底。
今天,这些诗词里的家国情怀从未褪色,只是换了模样。喀喇昆仑的风雪中,“00后”战士陈祥榕写下“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用年轻的生命把雪山守成春天;江苏灌云的开山岛上,民兵王继才夫妇32年以岛为家,把“家就是国”写成最朴素的日记;实验室里,军事科研工作者为攻克“卡脖子”技术熬白了头,他们说“我们的笔,也是保家卫国的枪”。这些故事里没有“金戈铁马”的轰鸣,却同样跳动着最滚烫的心跳,就像《诗经》里的士兵不会想到,他们“与子同袍”的誓言,会在今天化作“与国同行”的日常。
“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这些军旅诗词里的家国情怀,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选择:是战场上搭起的人墙,是边疆上挺直的脊梁,是实验室里熬红的双眼。今日的我们,不必都披甲上阵,却能把“家国”二字融进日常:它是认真做好一件事的踏实,是明知艰险却仍向前的担当,是见不得家国受辱的赤诚。他的热血始终沸腾,有时变成了你递出的热粥、我留的暖灯、他守的岗位。还有我们说起祖国时,彼此眼里亮着的光。(作者单位:平庄煤业老公营子矿)

 首页
首页 上一期
上一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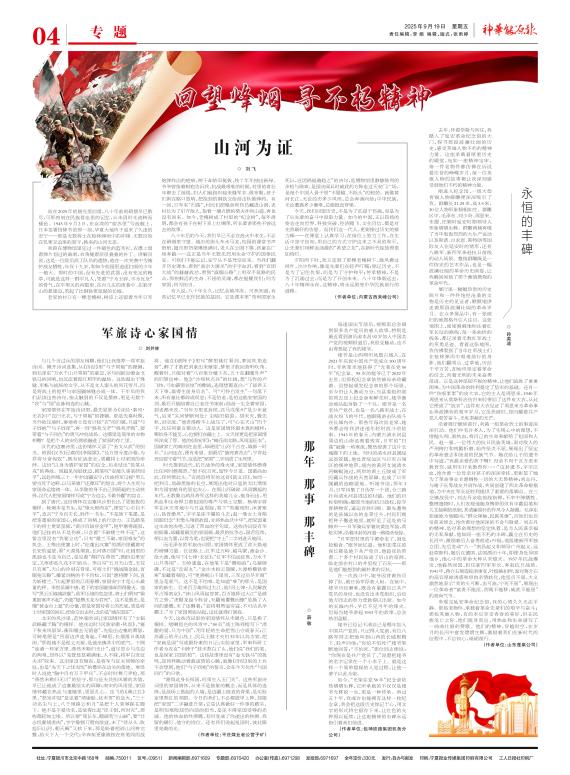


 上一篇
上一篇
